杨绛文集|杨绛的两个零——读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
【 杨绛文集|杨绛的两个零——读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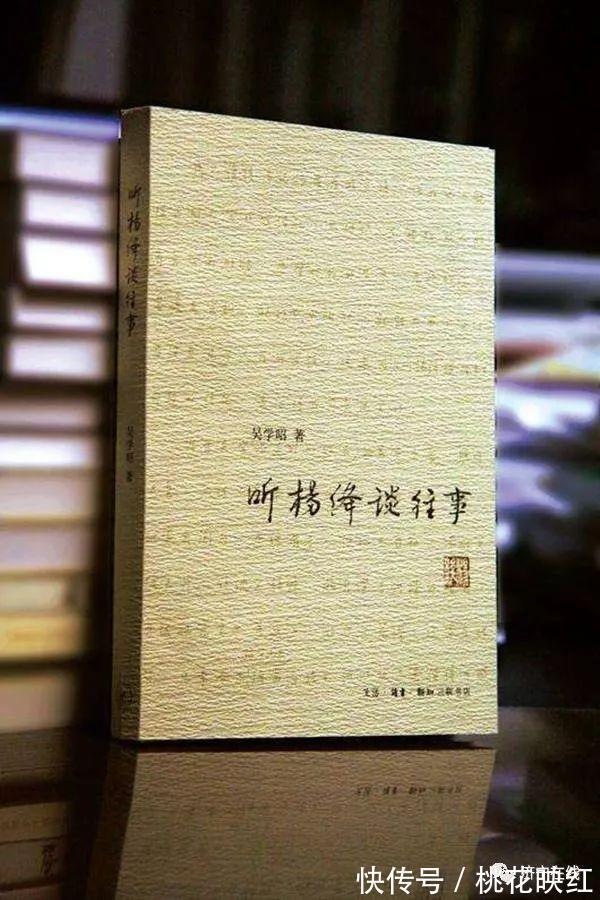
文章插图
——读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在美国波士顿的一个小镇读竖排繁体字的《听杨绛谈往事》,挺好玩。离大陆远,传主又是一位“心远”了六十年的人,读者的我便如站在人生边上看人生,有了可进可退、能入能出的通脱感。书前是时已九十八岁的杨绛写下的短序,清醒,清淡,说“没有任何奇异伟大的事迹可记”;书尾有作者吴学昭记下的长跋,热烈,亲切,也说传主“自称‘龟蛰泥中’”。不要说繁体字让人有了一种静和与古穆,单是两位女子静悄悄地梳理自己的头发一般梳理往日的岁月,就让人有了类似于幽谷听溪流的沉静、安祥、活泼、与喜欢。特别是十四章与十六章,光是题目就让人看了犯琢磨,一个是“我是一个零”,一个是“我仍是一个零”。其实,杨绛先生在北京的出场,却不是“零”的气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她进清华,仍然穿着上海时的旗袍,坐着人力车,还打着把遮阳的小洋伞。周围的女士们呢?几乎是清一色的列宁装,上衣有两排扣子,板板正正,配上灰色长裤,更是一片“革命者”的气氛。在这清一色里,旗袍洋伞人力车的杨绛,当然十分“惹眼”,惹眼得有些格格不入。她不管这些,只要自己喜欢与舒服,还有暗暗的下意识:不愿意跟风,不愿意随和,不愿意哪怕闪过一丝丝献媚的念头。“我”再小,也是我;“你”再大,也是你。虽然她似乎料到到了结局,她与她的钟书,都是典型的良民,“粗茶淡饭”甘坐冷板凳,“服服帖帖”叫干啥干啥,谁会为难一个本本分分的良民——但是,有些还是稍稍地出乎意料了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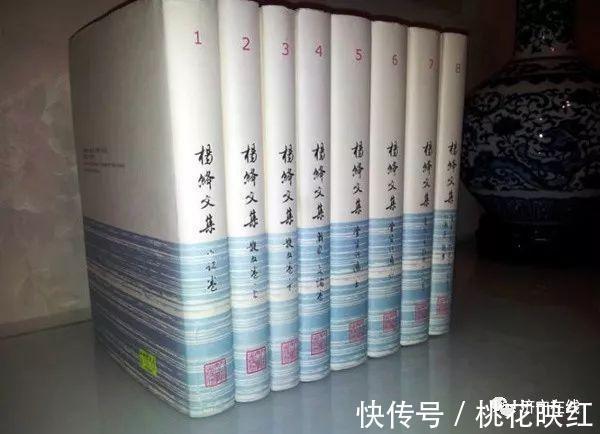
文章插图
自报公议评薪金(以多少斤小米计算),杨绛缩着不出头自报很少。少了也不行,说她有“散工思想”,不想为新社会多做事。从清华派分到文研所,头是何其芳,研究员们评薪定级,实际负责的何副所长大笔一挥,钱钟书二级研究员,杨绛三级研究员,与何有战友之情的卞之琳是一级。他们夫妻自得其乐,不在乎在些。一九五三年九月的第二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文研所的研究员全是大会代表,唯独钱、杨不是。他们不在乎,安全就好。外文组集体编写《西洋文学史》,不让参与者仅杨绛一人。不让参加就不让参加,可是重要的难题,甚至审稿,还让杨绛出力。所中的研究员全是编辑委员,只有出了大力的杨绛不是。是零就是零,她也不去为了不是零而额外花些功夫。不仅如此,遇到“革命观点”明显有违常识的时候,她还会站出来说鹿是鹿马是马。冯雪峰与何其芳辩论阶级性与人性,杨绛就忍不住出来说阶级不能概括一切,她问:红楼梦中的贾府四姊妹,同样的阶级同样的环境,为什么会有四个不同的个性?这个“零”是铁定的了。“文革”,在千万个零中,她更只能是零了。1977年之后,开启了多少人的好时代、新时代。杨绛呢?还是“零”。她有个简直就有些幸福感的说法:“从文学研究所一九五三年成立,到一九七七年改革开放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五年间,我是一个零。我开始有点困惑,后来觉得很自在,所以改革天放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零。”(《听杨绛谈往事·我是一个零》)吴学昭说钱、杨都“深自敛抑”。本该放开或曰绽放。可是他们却自觉地“深自敛抑”,从零到零。哪怕胡乔木、周扬等这些大领导有意提携,哪怕外国的国王盛情邀请,他们还是“深自敛抑”,力争敛抑到零。该书的最后一章是“逃——逃——逃”,逃到哪里去?连杨绛的“隐身衣”都无法做安静的归宿。而今,他们仨——钱钟书、杨绛与女儿媛媛——终于逃在了一起,可以从零开始了。
- 西装|《不会恋爱的我们》来袭,金晨化身霸总,恋上“小狼狗”王子异
- 唐寅|弘治十二年的那场唐伯虎科举舞弊案,吴宽信札揭露实情!
- 希腊人$古希腊眼里的中国,犹如“神族”一般,中国人看了都难以置信
- 园林&从王安石到陆游的诗句只过了一百年,扬州却成了宋金两重天
- 古诗词#关于王昭君的古诗词集锦
- 王之心&四本开局就惊艳读者的小说,一看书名就想入坑,书荒的你值得拥有
- 冷兵器#名字最好听的九种冷兵器,风翅镏金镗上榜,第一你绝对想不到
- 满山川@采撷日光的暖意,走进冬之素简
- 异途&庞大的反精英阶层让王朝由腐朽走向毁灭
- 我们的天才儿子|《我们的天才儿子》常来的浙图,浙图找出了他的翻译十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