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婶$当代散文||抹不去的记忆
文/金仁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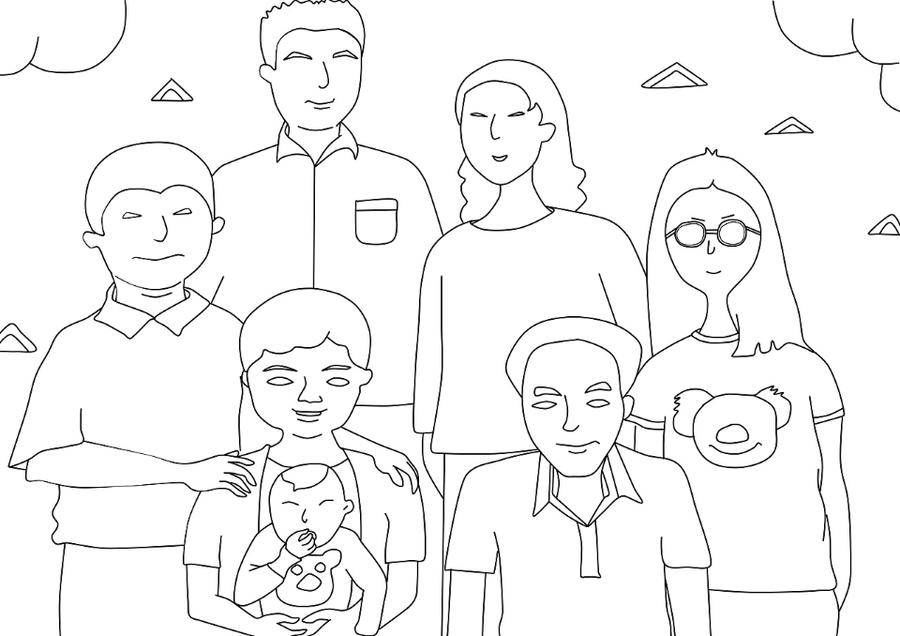
文章插图
大伯
我大爹是个棉匠,至于大伯解放前是如何到部队的在我心里却是个谜,因为几位叔伯与我父亲生前都未在我面前提及。我猜测最大的可能是生计所迫。
我羡慕大伯,因为大伯是个军人。一身军帽军装,立在哪,就是一副威武不屈相。解放后的军人离战争年月不远,加之政治需要宣传军人的勇敢及江山的来之不易,那时的军人差不多就成了“英雄”的代名词。当我读书时获悉军人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时,心里便想,真能践行这样的精神,还愁干不成一番事?
我敬佩大伯。他一生从未进过校门,却能与人通信。他写的信虽很短,几段话,长的段落话也不多,其间还夹杂着错别字,但,这是一个文盲在战争间隙自修自学的成就。他的裁剪技术也是在部队自学的,以至退休后还被桐城的一家服装厂聘为技师。都道部队是大学堂、大熔炉,我曾受大伯的影响,辍学后就诞生过从容报国的愿望;可惜我是家中独子,父母硬不答应。
至今我仍念想大伯。从上海一零一厂退休后,他学会了太极拳、太极剑,仗剑而行,一副侠客形象。几次客居我家时他都带着剑,在门前修习,引得庄上人围观。习武之人重道德,讲情义。有年我送他从安庆返沪,买好翌晨的船票,时间还是上午,大伯兴奋地带着未满二十的我到他安庆的老战友家,郑重向战友介绍:“这就是我的小侄子。”是夜,我陪大伯在安庆住了一宿,临睡前,大伯看着我脱鞋、解衣,塞给我两张拾元人民币,说,回去买双新鞋,买件新衣。那年头拾元钱是个大数字,翌晨,临上船分别,在检票口,又硬塞我拾元,说,回去买条新皮带。却不料,那平平常常的分别竟成了我与大伯的永别!
我更怜悯大伯。前任大妈因故改嫁后育有五个子女,大伯得知后才明白是自己无生育能力。我非医生,不知大伯的不育症与他过的残酷的战争生活有没有关系。大伯一生无儿女,我本想等我条件稍好即接他与后任大妈回乡下过,不料一九八五年国庆那天,大伯猝死于脑溢血。
但,现今的我对大伯曾参加的战争却并不完全赞同——“一将功成万骨枯”。大伯能在枪林弹雨中的存活固是个人的幸事,可那些枯了的万骨、他的那些战友们却是不幸的。他们活着时也有自己的亲人、爱人与家人,为何非要万骨皆枯?战争不是游戏,那是不尽的牺牲与苦难,是国与家共同的不幸,更何况现代毁灭性的战争。如果不是反恐,各国和平相处真的就那么艰难?可我转念又想,那时如果不是那些死去的战友拼了性命,和平的日子也真难以到来。——“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和为贵”。这,都是中国古语。
二叔
闲暇整理旧箧,见三十多年前二叔写给我父亲与我的信,毛笔小行楷,清超绝俗,藏锋恰到好处又妙不可言。舍不得丢,仍珍藏着。
二叔给我的信共有十三封,却惜二十多年前拆老屋建房时不慎佚失。那是他得知我因贫辍学,再三鼓励我自学,并告诉我他自习书法的经验与心得。二叔的字结体奇特,间架严谨,显然是临过魏碑的。我曾偷空临过几个月的帖,个中原因就是羡慕二叔的字。后来二叔知我决定自习走钢丝绳的文学,给我的信就少之又少了。我曾猜想:二叔或有让我完成他未竟事业的想法。
二叔是解放后的中专生,农校毕业,在当时算是高学历。五十年代,他与二婶都曾在乡下教过书,但无奈那时的政治风云激荡变化,他的工作也随之变动不居。从安庆调到蚌埠,又从蚌埠调到现今的滁州,临退前是滁州市种子公司的机关秘书。能在他的那样的一个时代坚守书法,足见二叔不肯与病态时代的病态人们同流合污,你争我斗,他胸中自有他的理想。“书如其人”,意思是人品决定书品!
- 杨晓通&“当代女马可·波罗”意大利文讲述侨乡浙江瑞安非遗
- 袁侃@当石库门遇上当代艺术,来今潮8弄体验一场“城市奇遇”
- |当代著名书法家姜军书法作品欣赏
- |“当代女马可·波罗”意大利文讲述侨乡浙江瑞安非遗
- 苏轼|西湖记想苏东坡
- 陈伟@当代最具收藏价值艺术家——陈伟 作品展
- |当代最具收藏价值艺术家——李金占作品展
- 苏东坡#西湖记想苏东坡
- 礼乐文明|解读丨“通情达礼”的当代启示
- |当石库门遇上当代艺术,来今潮8弄体验一场“城市奇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