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刊|频频被抵制的书籍:“取消文化”是欧美出版圈的危机还是转机?| 文化( 三 )
这也是许多将这些抗议行动称为“取消文化”“出版界猎巫运动”的人们所提出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认为,一系列的出版抵制运动打着维护多元主义的旗号,到头来却窒息了出版领域的思想多元。不过,考虑到出版行业本身的公共属性,这些对抵制运动的批评就需要得到更复杂的审视。正如哈歇特员工在面对伍迪·艾伦回忆录出版一事上的表态,出版自由的边界并不那么容易轻易界定。Medium2019年7月的一篇专栏文章就指出,在这个“全球互联”的世界,“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让自己的观点被‘世界’听见”。作为一名公开出版作品的人,“您可能意在与特定的人群交谈,但不能错误地认为,您说的话对那些您无意中冒犯了的人来说并不存在。”在一个出版的影响力日渐扩大的年代,言论本身可能造成的冒犯需要得到更为慎重的考量。
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社会许多其他领域的抗议运动一样,出版界这一系列针对作品的抵制运动也确实暴露了许多出版业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纽约客》2019年的一篇报道调查指出,在美国出版界中,编辑的种族比例严重不平衡,而根据2015年Lee & Low Books 的一项调查,直至今日,有色人种在进入出版行业时依然面临种种无形障碍。文章认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美国出版物关注重点的偏向。出版圈的一系列抵制运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一趋势的反拨。
运动的抵制者们常常提及“自由”,美国政治学者海伦娜·罗森布拉特在《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一书中,提醒我们需要审慎地理解这一词的使用。在某种意义上,与“政治正确”一词遭遇的处境类似,“取消文化”同样是一个带有污名化色彩的称呼。美国社会活动家艾肯·奥拉就曾在有关“苏斯博士”的争议中撰文表示,出版商仅仅是“召回”而非“封禁”苏斯博士的争议作品。这是一种温和的修正,而非“封杀”。而追溯历史,诸如《哈代兄弟》(Hardy Boys)等知名作品都曾因涉及种族歧视问题而经历修改。在作家Ellen Oh看来,称这些批评是“封杀”是言过其实,这种批评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在Ellen看来,如果观察舆论对这类作品的反应,会发现大多数的言论都并不希望这个作品被“驱逐”(call out),而是希望其能在修正内容后被留下(call in)。当一名受到同类争议的作者公开道歉并选择暂时撤回她的作品时,网上出现了许多支持并鼓励她归来的言论。相反,是“取消文化”的命名激化了对立双方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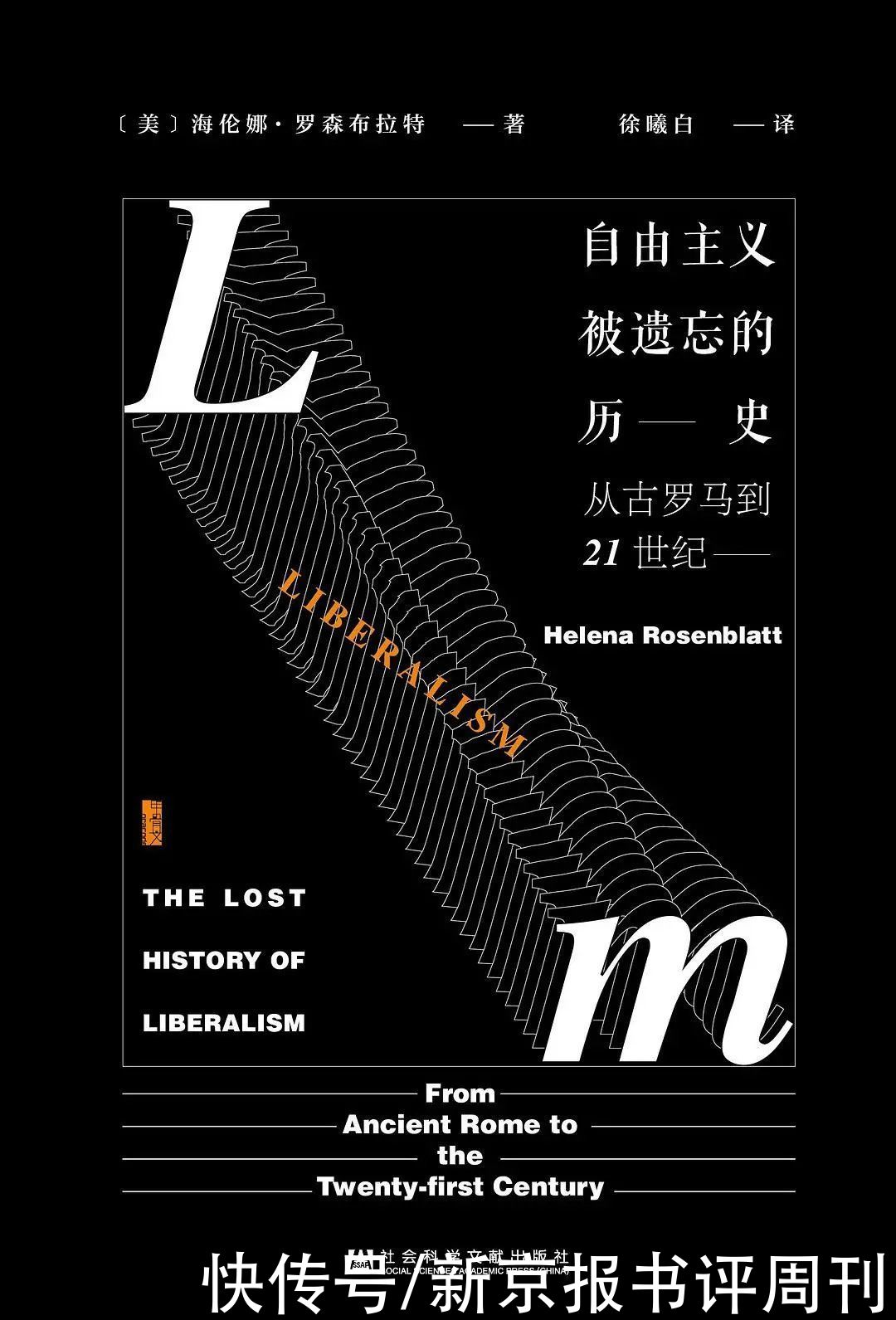
文章插图
《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美]海伦娜·罗森布拉特著,徐曦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0月。
耐人寻味的是,据BBC报道,去年年底,一位名叫朱莉·伯吉尔 (Julie Burchill)的作者特地撰写了一本主题为“取消文化”的书,但该书的出版商随即发现作者在 Twitter 上被指控有“伊斯兰恐惧症”,随即暂停了该书的出版。出版商认为,伯吉尔在与他人的争论中显露出明确的“对宗教的冒犯与越界”,布朗说她的评论“从道德或智力的角度来看是站不住脚的”,并且“越过了种族和宗教的界限”。由于“取消文化”一词的严肃性和攻击性,出版商认为它有可能成为伯吉尔表达自身偏见的一种掩饰。
今年,专栏作者亚历克斯·谢波德(Alex Shephard)在《新共和》发表了《出版意味着什么?》一文,其中同样提到了“取消文化”或许成为了一些出版商掩盖自身偏见的保护伞。诸如Simon & Schuster出版彭斯等的作品,是在公开支持一位倡导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仇外心理、厌女症、反犹太主义的核心人物,并从中获利,此时,言论自由并无法保证“意见的多样化,而是巩固了偏见”。同样,今年6月,一位出版巨头的经理对《卫报》表示,他觉得现在的出版商常常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矛盾”,即每个工作者都“支持多元化,但是一种他们‘想要’的多元化”。
- 和尚&司马迁记载奇案:和尚巧遇命案无辜被冤,县令发现破绽智破命案
- |男子钓到一条4.3斤的草鱼,没想到却被警方刑拘!爱好钓鱼的要留心了!
- 迪士尼公主@九岁男童笔下的迪士尼公主,艾莎和安娜被丑化,爱丽丝公主最相似
- |被名字耽误的冷门专业,其实是个宝藏
- 珍宝$千年古墓被光顾,盗墓贼少挖5厘米,却错失10吨珍宝
- 倪匡&古龙出上联:“冰比冰水冰”,金庸:此联不通,下联却被网友对出
- |人到30岁,被领导和小人针对,你要掌握这三条反击的策略
- 画风!霍春阳:被画坛冠以“霍家鸟”的美誉,将文人画的雅致完美复刻
- 人物@108将中,有9人被金圣叹评为上上人物,其中有哪些人配不上
- 日心@达芬奇为何被质疑是穿越者?你看他当年的手稿有多超前,就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