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卢姆&同情之书:没有同情心,是一种“恶”吗?( 二 )

文章插图
《恶的科学》,作者:[英] 西蒙·巴伦-科恩,译者:高天羽,版本: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
与同情一样,“邪恶”也是持续被人们讨论的话题。这两年国内的出版市场中也集中出现了一批专门讨论“恶”的作品,例如史文德森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关于邪恶的哲学思考》,詹姆斯·道斯的《恶人:普通人为何变成恶魔》等。与其他作品相区别的是,神经科学家西蒙·巴伦-科恩的这本书,将“共情”置于邪恶讨论的中心,这本书的研究也为前文提到的布卢姆多次引用。
科恩用大量的实证研究向读者展示,“同情腐蚀”是人们做出残酷行为的重要原因,那些做出在世俗意义上极端邪恶之事的人,共情水平常常很低。共情能力高低并非决定一个人是否作恶的全部,但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它处于最核心的位置。围绕共情能力这个圆心,外围的影响因素依次包括威胁感知、文化、意识形态、从众效应等。科恩也在此特别提到了著名的“平庸之恶”,由于恶行背后这些复杂的影响因素,因此艾希曼的恶不纯然是“平庸”的,除了社会因素,个人的同理心在艾希曼的行为动机中也占据很大的比重。
本书的研究也揭示了可能为恶者的一些性格特征。被他称作“零度共情”的人是做出残酷行为的高风险人群,他们往往对于“挣脱时间”有特殊的青睐,简而言之,他们厌恶情绪所代表的“流变”,试图能与理性的秩序相连。科恩特别提醒,在我们当下的教育中,对理性、秩序的强调还是远远胜过对同理心的培养,这值得我们警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恩对人文学者们用思辨的方法讨论邪恶这一话题颇有微词,他试图用这本书“将与邪恶有关的讨论带离宗教玄思的领域”。恶并非一种缥缈的属性,而是有其生理和心理的基础。不过同样,具备某些心理特征——比如共情能力的缺失,也并不天然给这个人打上“恶”的标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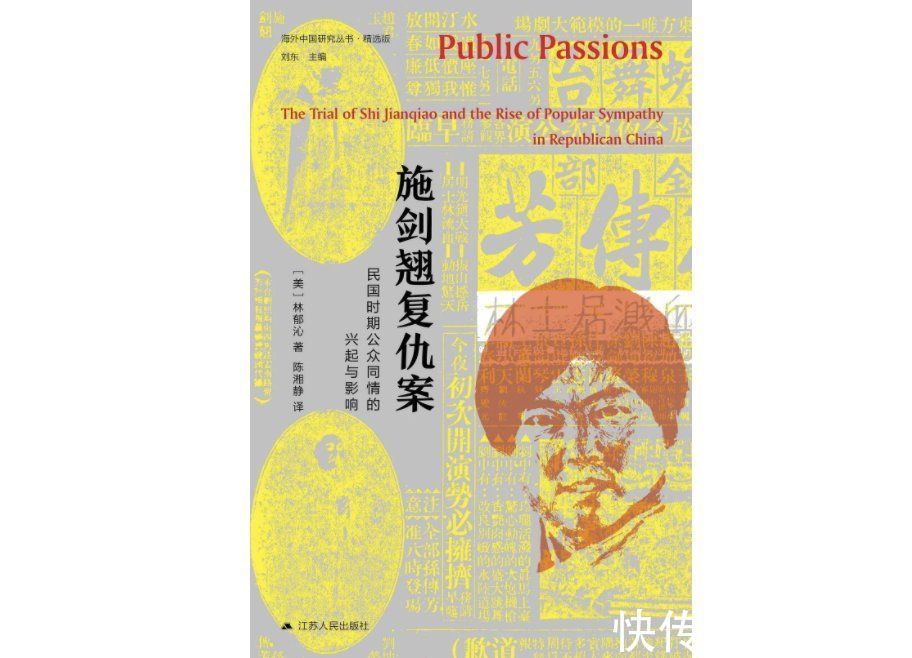
文章插图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作者:[美]林郁沁,译者:陈湘静,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年10月。
【 布卢姆&同情之书:没有同情心,是一种“恶”吗?】与前面的作品相比,汉学家林郁沁的这本著名的《施剑翘复仇案》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审视了“同情”。1935年,“民国侠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事让世人震动。在一场诵经仪式上,施剑翘用手中的勃朗宁手枪对出席的孙传芳突施冷箭。刺杀成功的施剑翘镇定地宣布:大家不要害怕,我只是为父报仇,绝不伤害别人,我也不会跑,紧接着投案自首,一时间站在了公众舆论的中心。
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述,本书副标题中的“公众同情”,与现在人们日常语言中使用的同情词义有所不同。在当时的语境中,这个词毋宁说与“舆论”、“国民情感”相混同,是集体性的。林郁沁通过这一案例的精彩挖掘,呈现了一系列与“情”相关的事件:施剑翘为父报仇过程中争取公众同情的策略,刺杀事成后媒体和民众的反应,文化精英们围绕这一行为呈现的两极评价。这些事件的背后,体现的是情感在中国现代公众诞生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被施剑翘的刺杀行为激发出的公众同情,实质是与性别规范论争、法制改革与法外正义、国民党威权统治等公共话题相关。这部作品讨论的重点并非“同情”的心理活动机理,而是其作为一种公共情绪时所具有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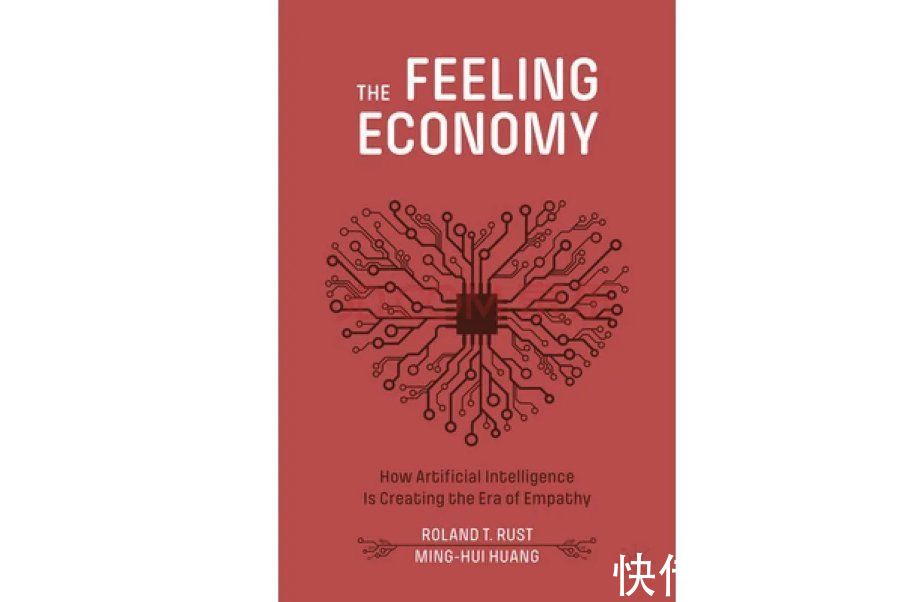
- 杨晓通&“当代女马可·波罗”意大利文讲述侨乡浙江瑞安非遗
- 打击乐&戏曲、交响乐、打击乐、古琴 中山公园音乐堂10场演出欢度春节
- 园林&从王安石到陆游的诗句只过了一百年,扬州却成了宋金两重天
- 错换人生&谁家子弟谁家院,“错换人生”DNA再掀波澜
- 王之心&四本开局就惊艳读者的小说,一看书名就想入坑,书荒的你值得拥有
- 和尚&司马迁记载奇案:和尚巧遇命案无辜被冤,县令发现破绽智破命案
- 异途&庞大的反精英阶层让王朝由腐朽走向毁灭
- 船夫&新科状元乘船回家,船夫随口说出一上联,状元却至死都没对出来
- 玉真子&金庸《碧血剑》八大顶尖高手排名,何铁手第八!
- 冬奥&青年艺术家走进怀柔山村送春联写福字,冬奥元素融入乡村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