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圣贝纳迪诺县法院,米勒案开庭了。来了很多人,挨挨挤挤,法院的玻璃门都被挤碎了……大家早上六点就开始排队,女大学生们一整晚都蹲守在法院,带了很多全麦饼干和低糖饮料。”
在最狭隘的层面上,这段描写对案情毫无意义。但直觉告诉我们,它和米勒案息息相关,因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一个人的快乐可以是另一个人的痛苦。露西尔·米勒被判有罪后,她忠诚的捍卫者桑迪·斯莱格尔尖叫道,“你们每个人都是杀人犯”,而经过长镜头洗礼的我们知道,桑迪说得不全对,但也不全错。上帝狄迪恩仿佛在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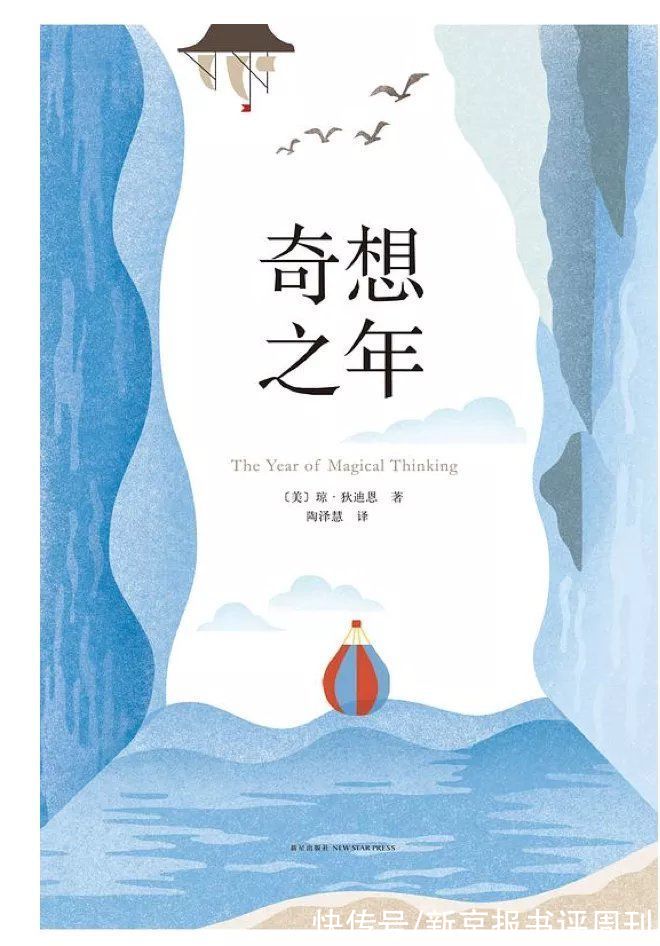
文章插图
《奇想之年》,译者:陶泽慧,版本:新经典|新星出版社2017年1月
怜悯的最高形式可能是讽刺。这点在《拉斯基同志,美共马列分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篇不足六页的短文是对主角迈克尔·拉斯基的人物速写,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位信仰马列共产主义的洛杉矶青年的形象。时值1967年,麦卡锡主义的热潮已退去十年,曾在美国盛行的共产主义式微,拉斯基这样的青年已成为少数派。他坚定的热情与实际的影响力形成巨大反差,“五一劳动节他组织的游行只有寥寥十几人参加”。然而狄迪恩喜欢这位患有轻微被害妄想的青年,喜欢他与世界的格格不入,喜欢这种“因为非常尖锐的恐惧而投身于注定失败的极端事业中的人”。
她将这样的欣赏藏在文末工人国际书店发生的一幕。一天结束,拉斯基和几位骨干像“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一般,回顾《人民之声》小报的销售情况。
“西蒙斯先生——同志,总收入是多少?”
“九美元九十一美分。”
“卖了多久?”
“四小时。”
……
“最大捐款额?”
“六十美分。”
“最小?”
“四美分。”
像这样,呈现而不点评,让意义在事实中浮现。这种写法让狄迪恩与读者保持距离,赋予她的文字以“冷感”。与此同时她又极“热”,从不惮于在写作中袒露自我,高度忠实于自己的喜好和趣味。1976年,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随笔《我为什么写作》中,狄迪恩写道,“Why I Write”三个词共享了一个音节,那便是“I”(我)。“我写作,完全是为了弄明白我在想什么,我在注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以及它具有什么意义。我想要获得什么,我对什么感到恐惧。”在伯克利读书时,她意识到自己不擅长学院式的思考,“不是思想世界的合法居民”。“我的注意力总是在边缘,我能看见、尝到、摸到什么,比如黄油和灰狗巴士……我只知道我不是什么,我花了好几年才发现我是什么。”
03
《向伯利恒跋涉》为何成为非虚构经典
狄迪恩是擅长描摹外部世界的作家,但最后落于纸上的图景无一不经过她记忆的筛选——归根结底,她凝视和刻画的是自己的心灵景观。这也是为什么,她最好的早期作品留给读者的不是某种洞见,而是某种印象;我们感受到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它在目击者心中留下的烙印。
在名作《向伯利恒跋涉》中,除了开篇“中心再难维系”的笼统慨叹,狄迪恩并没有对加州嬉皮士间蔓延的毒品和暴力问题进行深入挖掘,也没有试图通过采访专家权威,对整个社会体系进行分析。(事实上,她对警察的采访很快就遭到阻挠;她的部分采访对象也对她所代表的媒体怀有戒心。)如她所说,她并不是一个以思考和分析见长的作家,起码在这一阶段还不是。但她对视觉意象的痴迷和信任,恰好为当时的新闻报道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她所做的,是跟随这群人参加集会,在他们家聊天,参与观察他们的生活,客观冷静地记下她和他们之间的互动与摩擦,却对自己可能陷入的危险只字不提。她深入参与却高度疏离,将自己作为容器。
- 弗兰肯斯坦@苏联制造20条双头狗,冷战对手不甘示弱,美国人又制造出什么?
- 约翰·辛格·萨金特@美国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油画人物作品欣赏
- 美国世界艺术家协会!艺术家毕丽国画作品赏析
- 上流社会@美国最伟大的插画家,记录了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纸醉金迷的情景
- 虺文忠$《狄仁杰》里的虺文忠的组装兵器竹筒刀, 其原型是现代武器
- 连衣裙|美媒列出了在美国各州出生的球员中,能代表他们州的NBA球星
- 斯图尔特@美国最著名的肖像画家之一:吉尔伯特·斯图尔特
- 美国#美国画家亨利法尼专注于描绘美洲印第安人和记录印第安文化
- 道教#美国人是如何学习道家的?
- 狄更斯@《雾都孤儿》:人这辈子,谁也逃不出“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