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在对爱惶惑的今天,重读三位女性读书人的爱情( 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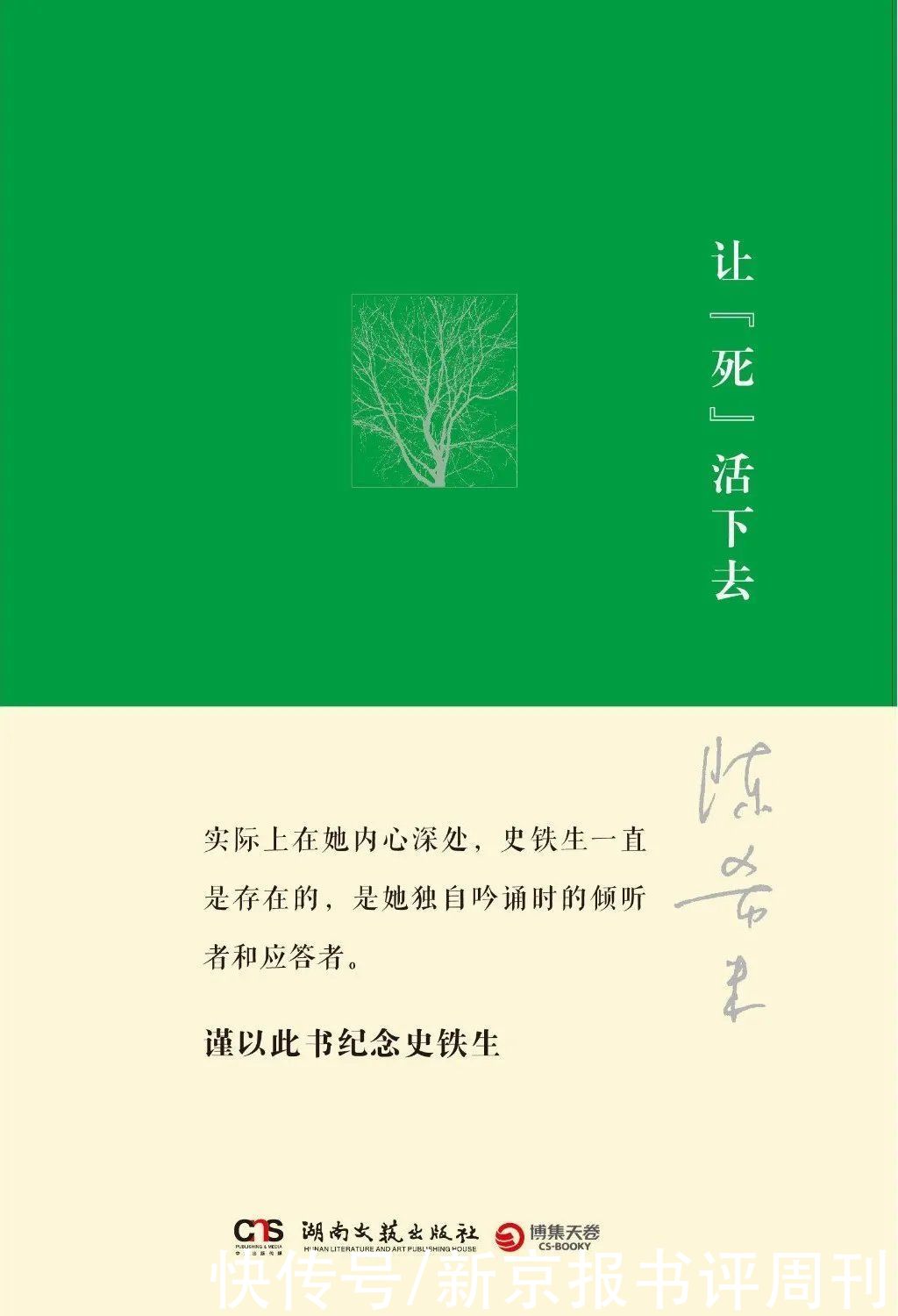
文章插图
《让“死”活下去》,陈希米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
另一则,是陈希米在她的回忆录《让“死”活下去》的开头,记录了2010年最后一天,也是她丈夫生命最后一天的场景:“谁也不知道那一天会是最后一天……在你进了手术室等待做器官移植之后——事实上,已经意味着永远没有了你。我居然还可以跟别人大声说话。你做得滴水不漏,最后一天离开;嘎巴死;顺利捐献器官。……我们说过无数次的死,终于来了?我终于走进了你死了的日子?”(《让“死”活下去》p2-3,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爱欲与死亡是思想领域里常谈常鲜、魅力无穷的论题。但是,这一纯粹的沉思,在这几则经验性的引述面前,显得颇不合时宜。无论她们是谁,她们的丈夫又是谁,都不妨碍上述“爱人之死”的场景扑面而来的冲击力。爱人之死无疑是一个人所有关于爱的经验里,最粗暴最复杂的一种经验,是爱的对象的彻底消失、永无寄托、空留回忆。这种经验的残酷,令哲学的沉思必须暂时退下,以避锋芒,并追问这几段爱人之死的经验到底有何特殊性。
简单来说,特殊性在于,爱对于死表现出了漫长而强大的耐受力,爱承认了死,包容了死,并超越了死。因为,死亡在这几个文本里并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事先张扬的结局,犹如命运已定的古希腊悲剧:徐晓在婚前就知道丈夫患有疑难病症,陈希米与轮椅上的丈夫通信十年后结婚,萌萌则几乎从一开始就沉浸在女性、死亡与爱的思考中,并在生命的最后与病魔搏斗了近一年。

文章插图
陈希米,1961年出生。1982年西北大学数学系毕业,供职出版社做编辑。图为她与丈夫史铁生。
死,并不是瞬间发生的事情,而是经过了无数次反思、无数次对话、无数次预演,生者甚至在爱人死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稍微具有生活经验的人都能领会,这种解脱感反而是爱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证明,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泪点。古人亦早已知道,山盟海誓的爱情固然美好,殉情共死的爱情固然悲壮,但“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能不能经历苦难才是爱的试金石。爱的激情,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冲动、浪漫和炽热感,而是承受苦难的不竭力量。
徐晓在丈夫去世后曾写道:“当死亡的事实离我越来越遥远,而死者的存在却离我越来越迫近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关于时间,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关于爱,需要你付出毕生的代价去体验,有所体验就够了,你甚至不要指望能把它们搞懂。”(《永远的五月》,见《半生为人》p32)
去体验,是关于爱和死最重要的意见。但即使不指望搞懂,也要进一步追问:萌萌、徐晓、陈希米等人与爱人之间这种爱的力量从何而来?为什么在这里,爱的激情不是电光石火的转瞬即逝,而是情感永无停息的脉冲?
02
爱的沉思
爱的激情仅仅是来自承受苦难吗?那么,如何定义苦难?苦难有的选吗?古往今来,凡间的大多数爱情,从头至尾都没有经历过称得上苦难的痛苦,难道就不是真实的吗?
苦难确实不容易定义,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往往没得选,被迫接受,而且你有很大的概率挺不过去。王安石写“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就可视为对苦难没得选的感悟。中小资产阶级在太平盛世里的经济压力、虚无孤独、“内卷”感之类并非苦难,只是高级一点的现代性焦虑。苦难总是围绕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打转转,有些是物质的,比如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活下去;有些是精神的,比如允不允许写诗,可不可以公开说话。
- 打击乐&戏曲、交响乐、打击乐、古琴 中山公园音乐堂10场演出欢度春节
- 纸杯#美术生在杯子上画“知否”,当倒入水瞬间,网友:居老师挺住!
- 郑兵$「诗歌欣赏」郑兵:那条河
- 海波东#斗破苍穹:云韵主题曲一出,拥抱结束,萧炎后悔在魔兽山脉当圣人
- 心学@心学大师王阳明龙场悟道,是如何在人生低谷,孕育出思想高潮的?
- 玫瑰|失业在家好久了,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 上海|在上海这些地方,足不出“沪”即可享受“年味”
- 陈珊|完美伴侣:没有家庭,事业成功的意义又在哪里?
- 作品展|郑海鸥艺术作品展在阳江市美术馆展出
- 中国传统文化#五月,一首诗站在窗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