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姆·托宾|许志强评《名门》︱与丹尼尔·门德尔松商榷( 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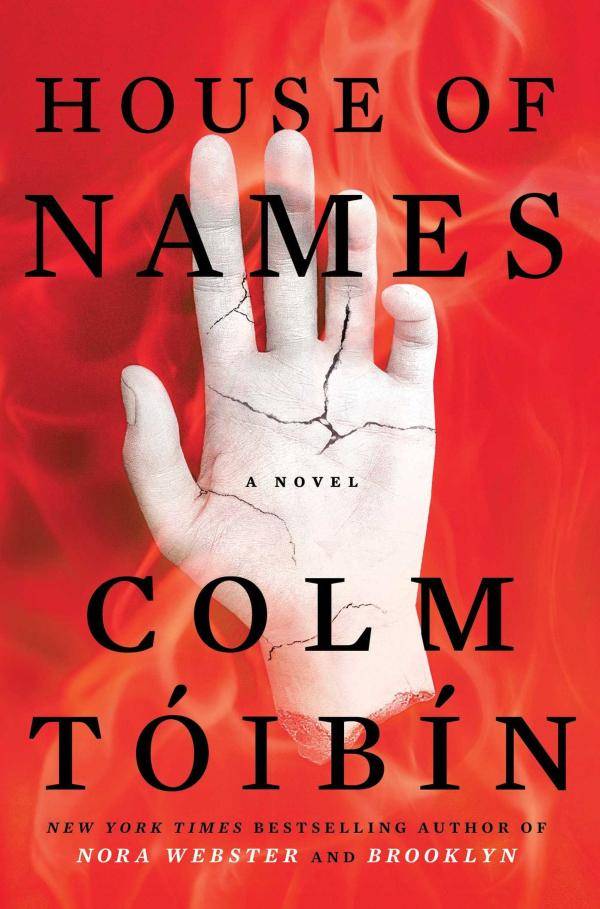
文章图片
《名门》英文版
三
门德尔松的口吻有时带点波俏 , 他的批评是严肃的 。 寓言和写实之间的关系平衡与否反映了创作逻辑的内在统一性问题 , 处理不当就会使改写失去可信度和力量 。 门德尔松告诫道 , 你不能在开篇写一场活人祭 , 接下来又赋予故事以“合理”的心理解释 。 如果剔除命运、神明、神的正义等超自然的、宗教的因素 , 那古希腊悲剧还剩下什么呢?恐怕就剩下一些“机能失调的家庭剧”了 。
类似的告诫和批评都是很有道理的 。 古希腊悲剧(或曰肃剧)的体裁属性有其自身的规定 , 与无神论的当代小说实难兼容;按照古典学学者弗洛玛·赛特林(Froma I. Zeitlin)的看法 , 到欧里庇得斯写作《俄瑞斯忒斯》时 , 悲剧这个体裁已经耗尽了潜力;欧里庇得斯大大偏离了神话形式 , 向属于现代小说的特性——“实验和变化”开放 。 门德尔松为托宾的创作寻宗认祖 , 指出托宾小说的欧里庇得斯性质 , 总之是想指出 , “当代主流小说 , 技巧上是写实的 , 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理 , 似乎并不是悲剧理想的载体” , 而《名门》的创作就证明了这一点 。
说到这里 , 门德尔松的观点已经介绍得比较多了;从体裁属性的本质看问题 , 他的看法是深入的 。 在此基础上我们不妨谈一点不同的意见 。
无神论倾向的小说与古希腊悲剧难以兼容 , 应该说这是一个常识 , 理由无须赘言 。 《名门》的创作是否要让小说成为“悲剧理想的载体” , 答案想必应该是否定的 。 托宾恐怕是难有这样一份雄心或痴心 。 取材于俄瑞斯忒斯故事的当代戏剧创作 , 尤金·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萨特的《苍蝇》等 , 均非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之复归 。 兰道尔·贾瑞尔的长诗《俄瑞斯忒斯在陶里斯》 , 谢默斯·希尼的组诗《迈锡尼守望者》 , 等等 , 以诗歌的体裁介入 , 只是一种再创作 。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讲 , 原典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有助于聚焦问题的某个方面 , 而且不乏启迪 , 但是过于刚性的强调则会弱化——甚至扭曲——再创作的性质 。
就说“头发”这个细节 。 考察小说的上下文 , 这只是一个寻常的挪用 , 并不包含欧里庇得斯那种戏仿的意义 。 《名门》设计了一个新的人物 , 名叫利安德 , 让他而不是让俄瑞斯忒斯来宣布流亡者回归 , 此种安排自然是与神话不符 , 但也谈不上是一种“拿文学模式打趣”的“后现代意愿” , 而是基于新编故事的逻辑做出的安排 。 在托宾笔下 , 利安德是年轻一代的领袖 , 在流亡者归来、歼灭埃癸斯托斯势力的斗争中扮演主导角色 。 以此断定小说是在“玩弄”神话传统 , 恐怕是有些断章取义了 。
从“头发”的插曲看 , 托宾的改写有挪用有杜撰 , 其实并不显示后现代式的反讽和取乐 。 批评家对后现代似乎有一种嫌恶心理 , 只要看到原典的意义失格 , 就判定新的创作纯粹是在玩闹 , 只要看到重述或改编偏离神话模式 , 就认为创作者是在给自己挖坑 , 因此其失败也是注定的了 。 此种立场的预设 , 加固一种厚古薄今的傲慢 , 却无助于认识再创作的逻辑 。 刘小枫对翁贝托·埃科(《玫瑰的名字》)的评论 , 大体也是传达这样一个理路 , 将后现代视为浅薄的文化表征 。
后现代的一大罪孽就是不作任何抗拒地承认诸神死了(或上帝死了) , 非但不作抗拒 , 甚至还乐陶陶地兜售无神论的文字游戏 , 由此可见其格调之卑弱 。 此种声讨 , 非只见诸于反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阵营 , 有时也出现在詹姆斯·伍德这样颇具包容性的批评家的文章中 。 后者对翁贝托·埃科的解构主义也感到不甚佩服 , 觉得那种世俗性的绝望感未免有些轻易 。 门德尔松谈及悲剧的体裁属性 , 觉得《名门》最难让人接受的一点就是太世俗化了 , 安于诸神的缺失 。 他抱怨说 , “即便在欧里庇得斯那种格调俗丽的修正主义的改编中 , 诸神及诸神的谋划安排也是显得很突出的” 。 因此 , 门德尔松说托宾“比欧里庇得斯还要欧里庇得斯” , 意思是说 , 令人遗憾的是托宾还不如欧里庇得斯来得保守呢 。
- 勒布朗·詹姆斯|詹姆斯的传球厉害吗?为什么皮蓬曾经评价他为天生的传球手?
- 纪尧姆·德桑格|一周艺术人物|隈研吾设计校园小丘,戴牟雨等联展“归山”
- 勒布朗·詹姆斯|职业生涯赛季场均得分从未低于20分的八名球员,谁的得分更惊艳
- 科尔迪奇@充满神奇潜力的梦幻世界——女画家科尔迪奇笔下诗意的神话传奇
- 穿衣搭配|关于詹姆斯你不知道的一些事情!颠覆了你的认知!
- 阿拉姆#探寻数千年前的文明联结
- 波兰|波兰科幻先驱莱姆:如果没有智慧,人类本可以进化得更完美
- 书评|波兰科幻先驱莱姆:如果没有智慧,人类本可以进化得更完美
- 勒布朗·詹姆斯|美媒列出了1983-84赛季以来,单场失误5+比赛场次最多的五名球员
- 南充|37岁的詹姆斯有多牛!不妨了解下联盟历史上那些伟大球员曾经的3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