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写诗需要热情,读诗亦是如此 | 海伦·文德勒的诗歌批评( 二 )
01
非理论的研究进路
亚拉巴马大学的诗人、批评家汉克·雷泽说,“作为文学的守门人,特别是在为《纽约客》写评论的时候,海伦·文德勒真的能把人放到文学的聚光灯下——使他们立刻成为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大出版社出版甚至重要学术职位的热门人选。她公开否认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但实际上,除她外不曾有人执掌过那样的权力。”
人们因此而尊重海伦老师,也因此而对她满腹牢骚。诗歌界的各路人士都抱怨过其感受力的局限。有人抱怨说她不喜欢实验。有人说她对诗歌的态度太过于学术。同时,文学学者又有些矛盾地认为文德勒女士跟他们的专业不沾边。
严格地说,文德勒的进路是非理论的:诗要么对她说话,要么不对她说话,而批评论说文是文德勒偏好的回应形式。她曾指出,“我的学位论文是关于叶芝的一些真正深奥的作品,当时我的想法是(我现在也依然这么想),如果我写的东西让诗人高兴,那么我做的事情就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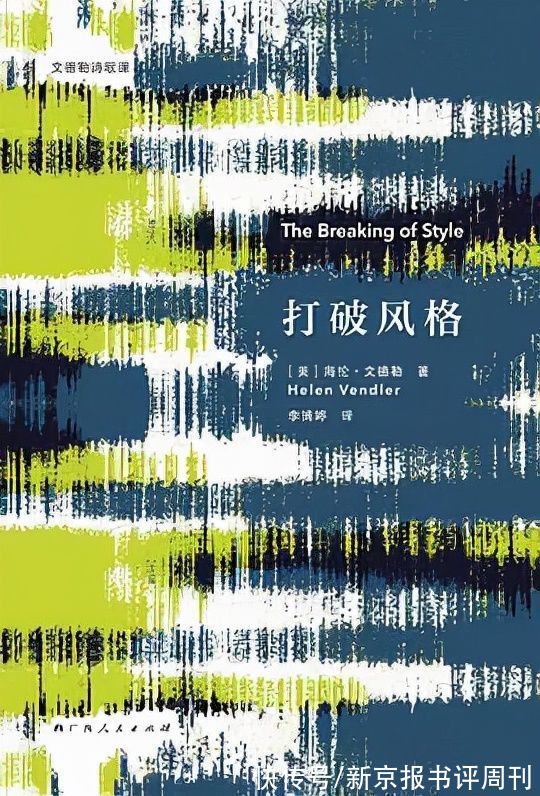
文章插图
《打破风格》,作者:(美)海伦·文德勒,译者:李博婷,版本: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
现在讨论作品的意义,几乎不会有学者认为作者的意图是最终标准。于是乎,文德勒想得到诗人认可的欲望看起来就更不寻常了——这与其说是专业标准的需要,不如说是个人的性情使然。也许,诗人之死,只是使这个挑战变得更有趣了。
近年来,文德勒一直以讲演者的身份在讲台上与诗歌进行越来越多的对话。
2005年5月,她在国家人文基金会做了年度杰斐逊讲座(这个荣誉包括10000美元的酬金)。2004年秋天,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的《诗人的思考:蒲柏、惠特曼、狄金森、叶芝》就以她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克拉克讲座为底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的《看不见的倾听者》,也是基于她在普林斯顿大学关于抒情诗的谈话修订而成的。
一开始,文德勒看起来只是陈力就列,扮演了一个新角色:做老一辈诗歌批评的政治家。但她的讲座本身,又相当于一个对文化素养状态和文学研究功能的庄严警告。
她坚持,阅读诗歌时,需要一种学者在匆忙冲向跨学科时丢掉的技艺和心态。这种担忧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又和最近现代语言学会流行的讨论攸切相关,那就是文学学者能不能对普罗大众解释自己所做的事情。
02
拒绝做“文学品位的塑造者”
文德勒不用电子邮件。某种程度上,这并不令人吃惊。花时间读读她的作品就会知道,这个女人的心思全放在了诗歌上,她一点儿也不为自己的书呆子气感到害羞。“我对群体没有兴趣”,在2000年纽约的一次小组讨论上文德勒说,“我从不加入政党。我从不投票。我从不登记投票。我从不去教堂。我也从来不属于什么俱乐部。我从来不属于任何团体。”倒是让想采访她的采访人员松一口气的是,她有一部电话。
如此一来,这就更惊人了:她形成期的智识经验之一,是随课堂技术的创新——投影仪——而来的。她还记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自己坐在黑暗的教室里的情景,当时,新批评的奠基者之一I.A.理查兹(I.A.Richards)会带着学生一行、一行地(有时还会一个词、一个词地)读诗。比如说,他会展示济慈的《希腊古瓮颂》的各个部分是怎样相互关联、修正和丰富彼此的。
这就是“细读”。在其早期学术著作中,文德勒也以这种方式分析乔治·赫伯特、叶芝和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她的视野令人印象深刻:不是每个学者都会认为自己有本事(逐一)谈论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的宗教诗人、一个用诗文来反映复杂的神秘学说系统的爱尔兰革命者,以及一个写抒情诗表达心智的内转和想象的冲动的美国现代主义者。
- 冯恩昌|【临朐印记】冯恩昌:?听琴与写诗
- 深思子&读书需要悟,书法需要悟,悟出人生
- 文化|英国创意与文化技能协会主席唐纳德·海斯洛普:艺术品市场需要在公共和私营领域之间创造更多平衡
- 年终奖|高校“录取规则”大变动,教育部已明确指示,考生需要提前知晓
- 哲学|不确定时代,我们需要哲学
- 毛笔@男子写巨型书法,百斤墨水一次挥霍完,一个印章还需要六人扛动
- 家人|越亲近的人,越需要你的尊重和耐心
- 癞蛤蟆!余秀华不顾批评继续写“黄诗”,可敬还是可耻背后隐情令人唏嘘
- 林妹妹$“林姑娘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贾母为何如此疼爱林黛玉?
- 金庸#金庸笔下那些奇葩的武学,需要付出奇奇怪怪的代价才能够修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