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丽娟:我发现您在提供给上海国际诗歌节的诗里有好几首是诗人之间的赠诗 , 可见您是一位特别珍视友情的人 。 我国古代文人一直有互赠诗文的传统 , 对此怎么看?您的诗可谓“古典与现代媲美” , 请谈谈在创作中 , 您如何做到古典与现代的共振?
西渡:唱和是中国诗歌中一个突出的现象 , 说明中国诗人对“诗歌共同体”很早就有深刻的领悟 , 诗在他们之间一直作为一种理解的力量发挥着心灵桥梁乃至心灵疗治的作用 。 按照存在主义的看法 , 孤独是人类个体的宿命 , 但诗并不认同这种宿命 。 一首赠诗是一颗孤独的心向另一颗孤独的心发出的邀请 , 和诗则是一种响应 , 在邀请和响应之间则是人类克服孤独的行动 。 这是人所能有的最高贵的行动之一 , 也是把孤独的个体挽留在世界上的温暖力量 。 但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 在我看来 , 唱和还具有超越个人情谊的更普遍的意义 。 我把每一首诗看作是一次召唤 , 一件赠送给世界的礼物 , 也是赠送给每一个人的礼物 。 可以这么说 , 已经存在的每一首诗都在呼唤它的和诗 , 而你写下的、即将写下的每一首诗既是对这种呼唤的应和 , 同时也是对另一首存在于未来的诗的呼唤 。 所以 , 诗歌共同体不仅是超越地域的 , 也是横跨古今的 。 对我来说 , “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悲伤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这一“诗歌共时体”的克服 。 作为诗人 , 我既生活在当代的诗人朋友们中间 , 也生活在这个由古今中外的诗人、诗歌构成的诗歌共时体中间 。 这使我感到幸运 。
古典与现代的区分是一个现代的观念 。 对于我 , 这样的区分即使有充分的理由 , 也是值得反思的 。 当我在少年时代开始阅读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孟浩然的时候 , 他们对我并不是古人 , 而是活生生的人类个体 , 真真切切地活在我的呼吸之间 , 也活在我眼前的自然中 , 与我分享着同一天地:陶渊明清澈的目光仍停驻在眼前起伏的麦浪上 , 李白飘逸的身影拉长了你饮下的每一滴酒液 , 孟浩然还在和邻翁讨论今年的收成……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 确曾考虑把古典诗歌研究作为终生的志业 。 只是因为写作的快乐最终超过了研究的乐趣 , 才使我放弃了这样的打算 。 我的诗作很多取材于中国的文学传统、神话、历史 , 但我的写作始终是面对当下的 , 我看重的是这些题材中在当下仍具有活力的部分 , 或者说 , 是题材中具有超越性、永恒性的部分 。 传统和现代同时教育了我 , 使我避免成为一个单向度的人 。 也可以说 , 我是非我 , 传统是非传统 , 现代是非现代 。 我、传统、现代这些概念 , 必须在它的本义之上加上它反面的内容 , 你才会对它的丰富内涵有较为透彻的领悟 。 斤斤于字面之义 , 诗和人都会失去很多成长的机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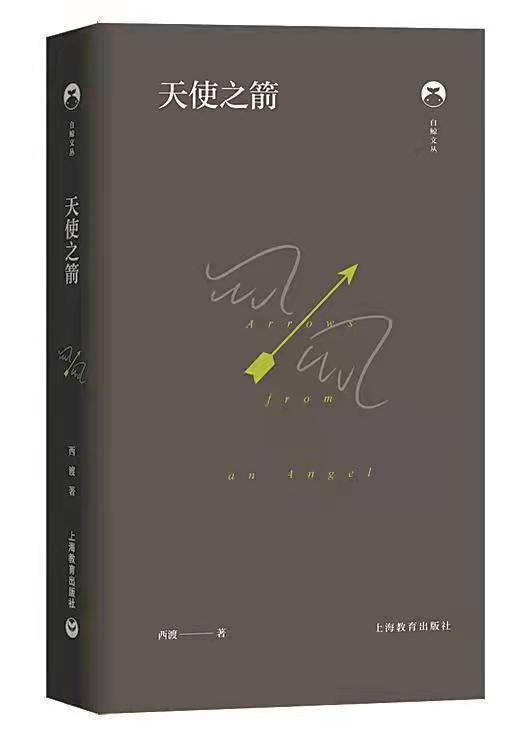
文章图片
崖丽娟:中国新诗走过了100年 。 近年来 , 诗坛众声喧哗 , 表面很热闹 , 但圈外对此未置可否 。 请问如何看待当下诗歌写作现状?怎么研判中国新诗的发展走向?您说过“诗人不必有大师情结 , 大诗人情结会把一位诗人提早毁掉” , 我在不同场合听人说起这句话 。 能否再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具体涵义?
【诗歌|专访|诗人西渡:诗是宇宙的语言】西渡:我感觉喧哗是1980年代诗坛的特点 , 1990年代以来诗坛实际上冷清了许多 。 这种冷清是一个沉淀的过程 , 也意味着成熟 。 这个沉淀的过程 , 既关联于作品 , 也关联于诗人 , 是两方面的水落石出 。 1990年代以来 , 诗人们成功突破了新诗写作的青春魔咒 。 新诗史上几个主要的诗人 , 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穆旦、戴望舒 , 其最好的作品几乎都写于30岁之前 , 一过30岁 , 写作的数量和质量都直线下降 。 当代诗人中最有成绩的十来位差不多都克服了这个魔咒 。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 90年代以来 , 诗歌在当代文化中的地位趋于边缘 , 但好诗人的数量、好作品的数量却克服了这一不利局面 , 呈现逆势增长的态势 。 1940年代最重要的诗人是“九叶” , 当然 , “九叶”之外也还有不错的诗人 , 但都加起来 , 这个数字也不会太多;1990年代与“九叶”相当的诗人 , 我们可以数出几十位 。 这也是很大的成绩 。 所以 , 我对新诗的未来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 。 我曾经表示过一个看法 , 目前我们可能处于新诗的“六朝时代” 。 什么是“六朝时代”?就是诗歌的各种可能性(诗意的、技艺的)不断被发现 , 诗歌的领地不断拓展 , 但诗歌的表现尚未达到圆熟的时代 。 这是顶峰之前的时代 , 但也是为顶峰做铺垫 , 准备条件的时代 。 显然 , 没有六朝的准备、铺垫 , 就不会有盛唐的顶峰 。 也许 , 我们的时代也正在为新诗顶峰的到来准备条件 。
- 江苏省军区#我与酒与美女诗人……!
- 郑兵$「诗歌欣赏」郑兵:那条河
- 诗歌|点赞近百万!这些小学生亮了
- 山水长&北宋诗人王安石彻夜难眠,写下一首忧国忧家的“静夜思”
- 里贾纳&读书 | 利尔本:诗歌让我们步出沉默
- 诗词#7位幸运诗人,只流传下来一首诗词,却成千古名作
- 一棵树|冬天,栽一棵树吧(诗歌)
- 梧桐@道尽人间悲欢离合及喜怒哀乐,以美取胜婉约派诗人李清照
- 白居易&唐代女诗人之首:才貌双绝,十六岁成为营妓,却以道袍了却余生
- 约瑟夫·吉卜林|被文坛严重排挤,英国诗人吉卜林十句格言,体现异样风情,收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