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思想非常活跃,妙语连珠,睿智而诙谐;跟他老人家交谈,没说几句就像坐热气球一样把你往上提升,文学、音乐、哲学……,梭罗、瓦格纳、佛朗克、哈代……,不知不觉就会谈上数小时,没有寒暄和客套,每次都是这样;好像他一生都是在从事这场纯粹的精神之旅,与人交谈是长途跋涉中的小憩,而他人的疲倦不支则会令他惊讶。
记得初次见面他就问我,中国古代画家中喜欢哪一位?我回答说是“倪瓒”。他颔首,说:“string quartet(弦乐四重奏)。” 便转身做了一个演奏音乐的动作,补充说:“他只使用小型乐器。”然后比比划划,说前景、近景、中景、远景相当于四种乐器的配合,等等。他的比喻令人耳目一新,而他说话的神态有几分孩子气。
印象中,他开口前总是笑吟吟地眨一下眼,好像是自己心里先乐了;表情略带腼腆,并无预想中的威严。他袖手侧身,轻言细语地“掼戏话”(这是我们湖州、嘉兴一带的方言,说俏皮话的意思),眼睛眨巴着向一侧看,像是在看他说出来的句子,盈盈然似有光彩。我记不住他说过的话,太多了,记不下来。郁达夫先生的文章里说,每次拜访鲁迅先生,回去路上想起先生说的某句话,都还忍不住要笑。我拜访木心先生也有这种体会。

文章插图
有一次交谈时谈到鲁迅先生,他起身像是去洗手间,侧过脸用上海话咕哝道:“同伊好比啊!”(跟他能比吗?)
说起五四文学,他总是谈周氏兄弟,尊他们为大诗人,认为别具一格的高超文体是一个方面,重要的还是他们的心性和思想。
说起诗歌,他说最称心的还是阿波利奈尔的无标点自由体诗,旧体的格律诗可以玩,但也就那么一点意思,平仄对仗傻里傻气的。
问他对当代诗人的评价,他说:“顾城好。”
问到绘画方面,他说:“我赞赏安塞姆·基弗、卢西恩·弗洛伊德、安东尼·塔皮埃斯……”
有一次他问我怎么看张爱玲,我回答说,人一格言二散文三小说四。
他听罢哂笑一声,默然不予认同。
他不喜欢争论,从不大声说话,交谈时很注意倾听。如果有什么说法当众忤逆了他的自尊或信条,他会昂然掉过头去,下巴颏扬起。
他一根接一根抽烟,烟灰长长的不去弹落,掉在了毛衣上也不掸拂。像波德莱尔,他衣着考究,精于修饰。言谈总是委婉而诚挚。深黑的瞳仁像光滑的丝绒。年逾八旬,他的眼睛还是亮的,清亮明净,富有神采。他满足了我平生的一个愿望:和诗人卓越的化身交谈。这是我的荣幸。可惜几次见面都未留下一张合影做个纪念。
最后一次见面告辞时,他让我等一下,说是给我看个东西。他去楼上卧室,过了一会儿拿着一张小纸片下来,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分享从新闻纸上剪下的一幅尼采临终前的肖像。我见过这张相片,尼采的胡须像皮鞋刷子,衣衫像理发店的罩布。木心先生用吴侬软语的普通话轻声说道:
“你看,他尽管是发疯了,可还是那么的伟大。”
这平平常常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是说,记忆中出现最多的是这个细节;他的语气、神态(那不可腐蚀的纯真),当时客厅里的光线,小镇午后惫懒的阳光,都还记得真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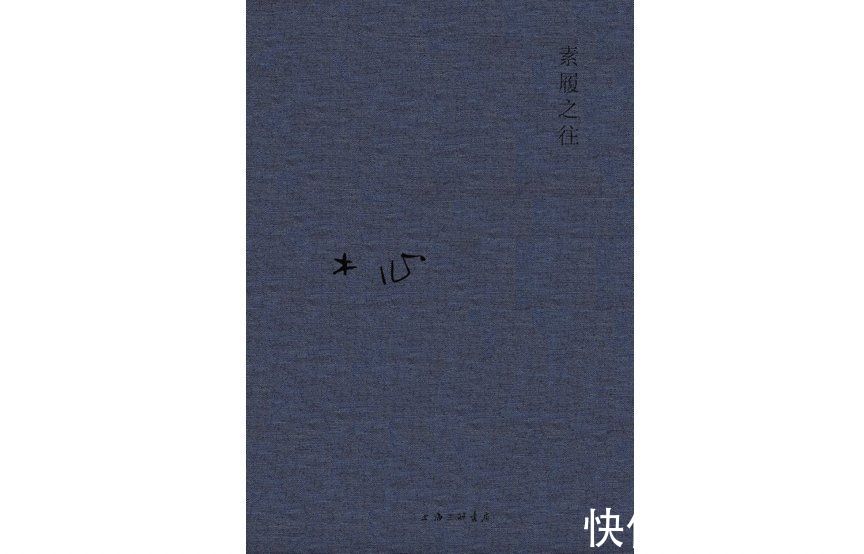
文章插图
《素履之往》,作者:木心,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0年4月。
象征主义的”入“和”出“
我在世纪之交开始接触木心先生的作品,是朋友周江林推荐我看的;此前从未听说过木心这个名字。也就是说,木心先生归国之前我就读他作品(复印件)、听闻其传说了。他是我心目中的大人物。
- |3枚一套的1角纪念币,现在市价达到了4000多,看看你有吗?
- 纪念币|今年还有4币2钞可以面值预约,更多题材可能发行,值得期待
- 塞萨尔·弗兰克|杭州爱乐乐团举行纪念塞萨尔?弗兰克诞辰200周年音乐会
- 观众|话剧《四世同堂》迎来第300场纪念演出
- 纪念币|虎年生肖纪念币亮相 贵阳市民踊跃兑换
- |法国作家司汤达逝世180周年,小说《于连》为何改成《红与黑》?
- 人物|话剧《四世同堂》迎来第300场纪念演出
- 纪念币|冬奥会币钞的二次预约信息,哪些人不要预约,哪些人不能兑换
- 清联|58岁当代楹联名家、中国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太品逝世
- 纪念币#法国纪念著名剧作家莫里哀诞辰4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