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清华#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如何促进了都市社会的发育?|专访阮清华( 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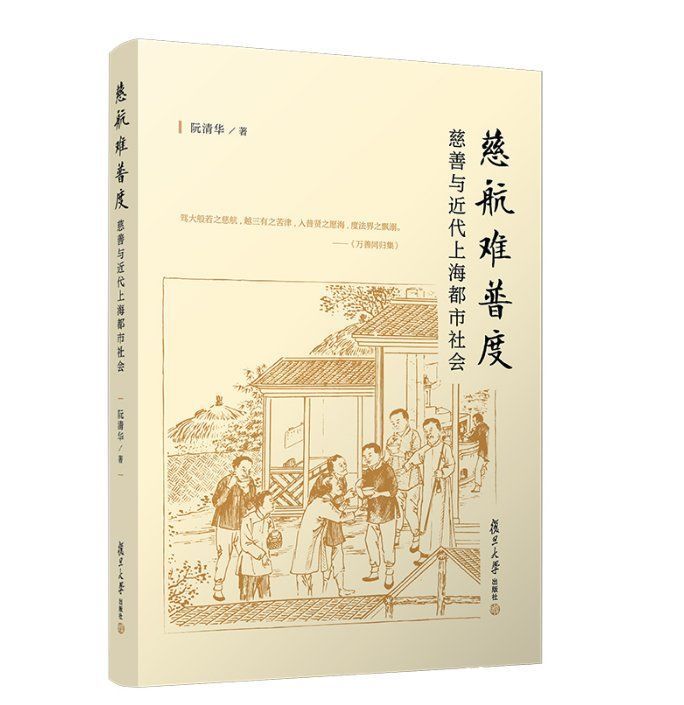
文章插图
《慈航难普度》,阮清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我们很难简单判断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到底是延续性更大,还是断裂性更大
新京报:在中国众多传统具有慈善功能的组织中,你为何会选择重点关注善会和善堂?与传统的官办救济机构、宗族组建亦庄、义学,移民组织的同乡会馆、同业公所和宗教组织办的慈善机构相比,你觉得善会和善堂有什么样的特征?与那些慈善机构相比,在实际的慈善事业中,善会和善堂扮演了多大的角色?
阮清华:我重点关注善会善堂,主要是因为看到这类慈善组织在进行救助的时候,对于受助者没有明显的地域、籍贯、职业和信仰等方面的规定,而是面向所有穷苦大众。宗族组织创办的带有慈善功能的义庄、义学等主要救助本宗族弱势者,一般不服务非宗族成员。同乡会馆自然主要为来自家乡的同乡服务,同业公所主要服务对象是本行业从业人员中需要救助者;当然,会馆公所在近代上海实际上有时候同时兼具同乡和同业性质,他们的救助对象同样有时候既是同乡又是同业者。宗教组织创办的慈善机构有部分主要服务于传教的需要,只救助那些接受其教义者,或者是潜在的信众;但也有部分面向普通大众,后者也是我所关注的对象。
中国官办救济机构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救荒救灾是历代王朝不能忽视的工作;此外,面向特定弱势群体救济的机构,历朝历代也所在皆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六疾馆,隋唐时期的悲田养病坊,宋代的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慈幼局,金元时代的普济院、暖济院,明清时期的养济院、惠民药局、漏泽园、栖流公所等,大都由官方设立或由官方支持和倡导兴建。而我所关注的善会善堂,是明清以来由民间人士兴办的慈善组织,用梁其姿先生的话来说,“是明清社会的新现象。”这类善会善堂在传统时代在功能上具有与官办救济机构互补的一面,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却重在重新界定社会身份等级,“诉求往往带着极浓厚的道德性。”当然,到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我认为这些传统慈善组织或者新建的慈善组织,其社会功能日益突出,而所谓道德性的追求可能有所减弱,或者说其关注点已经有所偏移。
善会善堂在整个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中扮演多大的角色,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方面,不同时期善会善堂和其他慈善救济组织的规模和影响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我们目前也缺乏对整个上海慈善事业的全面了解和研究,所以也很难进行量化比较。不过我们可以从几个数字去大致了解其时上海慈善事业的规模。1930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设立上海市慈善团体财产整理委员会,对全市主要慈善组织拥有的财产进行了统计。
小浜正子教授梳理这次调查结果后发现,其时上海28家主要慈善组织拥有的房地产总值高达1410万元。另外她也推算出1930年上海华人民间慈善团体财政开支规模至少为200万元,甚至超过250万元。当年上海市政府开支为708万元,公共租界工部局开支1950万元,法租界公董局开支为662万元。华人慈善组织支出规模约略相当于上海市政府的三分之一,相当于全市三个市政机构财政支出总和的百分之七。可见,华人民间慈善组织在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发展和维护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新京报:你说近代上海社会与传统乡村社会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但又不同于“城乡连续统一体”的江南市镇,是一个陌生而新鲜的空间。但是,近代上海的慈善机构和慈善理念,又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儒道佛的慈善理念之上,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你觉得上海的都市化如何改变了中国的传统慈善事业?总体上来说,对于近代上海慈善事业与传统中国慈善事业之间的关系,你觉得是断裂性更大,还是延续性更大?
- 秦简@清华简爆出上古猛料:蚩尤是黄帝之子?改写历史的竹简都藏在哪?
- 吕焕成#延续吴门画风,描绘人间仙境,吕焕成绘《春山听阮》
- 艺教中心@清华保洁阿姨,惊艳全网!
- 考上&父亲精神失常母亲常年卧床,儿子744分考入清华,如今他怎样了
- 清华#林徽因去世7年后,梁思成向林洙“求爱”,死前留给林洙8个字
- 版画!日本近代版画大师斋藤清冬日雪景系列版画作品
- 阮元!应该尊碑还是尊帖?阮元尊碑学说确立实为碑派书法能顺利推行而已
- 沙孟海!书法家白蕉,其书法响彻大江南北,近代写“王羲之”书法第一人
- 近代@日本近代版画大师斋藤清人物系列版画作品
- 顾学$蜀人钟子丨考史录:近代学人甘蛰仙与顾炎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