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人#没有做到“情不自禁的自我纠正”,它便难以成为优秀的儿童绘本( 三 )

文章插图
在绘本中图片对应的文字为:……那里还有一些伐木工人。他们每个周六晚上都会拥进城里,制造出大量的噪音,而且有时候还发生各种打架斗殴。他们简单吓坏了我的母亲。
但另一方面,殖民者的视角又确实存在。

文章插图
在绘本中图片对应的文字为:他有一个黑奴和两条狗……
1994年,本书出过一次修订版。新版对两处细节作了改动,一是将作者用以形容印第安人的“tame(被驯化的、驯服的)”一词(常用于形容动物或物品)删去;二是上图这段话,原版是这样的:“他有两条狗和一个有色人种男孩。狗的名字叫塞克斯图斯·霍斯蒂利乌斯和努马·庞皮利乌斯。那个有色人种男孩和我父亲年纪差不多。他是个奴隶,但他们没有那样叫他。他们只是叫他迪克。(When my father was very young he had two dogs and a colored boy. The dogs were named Sextus Hostilius and NumaPompilius. The colored boy was just my father’s age. He was a slave, but they didn’t call him that. They just called him Dick.)”改成了“他有一个黑奴和两条狗。那两条狗名叫塞克斯图斯·霍斯蒂利乌斯和努马·庞皮利乌斯。那个黑奴男孩和我父亲年纪一样大,名字叫做迪克。”
显然,编者认为这两处表达将对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的物化、矮化和早已被科学抛弃的“人种分类法”自然化、合法化了,因此作出了删改。
此外,涉及祖母的内容只有两页,且无关个人成长,只写了她嫁给祖父生了很多孩子,以及那句不断重复的话“他们辛勤劳作,他们坚强而善良”;本书写到六位长辈,其中三分之一篇幅给了参加南方军的父亲。可见这部书在性别维度的表现上也很值得打个问号。

文章插图
在绘本中图片对应的文字为:当我母亲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有一些印第安人也在明尼苏达州。我的母亲并不喜欢他们。他们连门都不敲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厨房,坐到地板上。然后,他们就会揉着他们的肚子,指着他们的嘴巴,表示他们饿了。他们会赖在那里不走,直到我的母亲的母亲给了他们一些吃的。
另有一段更有趣的,虽然文字说年少的母亲厌恶印第安人,但画面中却由女性黑奴举着扫帚赶走土著,白人女孩远远望着他们,双手干干净净如同她的道德一般“无暇”;下一页里她又被喧闹粗鲁的工人“吓坏了”。
作品数次重复母亲是“安静而温文尔雅”的,她被送到修道院,她喜欢修女们的“温和、从不大声说话”,她跟着修女学习画画、四门外语、美丽的刺绣和管风琴,她还有时间学习养花和照顾动物……如此对比之下,叙述母亲的“干净文雅”很难不让读者感觉微妙复杂——当作者的直接判断(往往是十分确信的样子)与文本呈现乃至历史信息之间的裂隙太大时,读者很有可能会陷入“一时之间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在反讽”的困惑之中。
当我们注意到黑人男孩身上的补丁和手里的大包小包,了解印第安人和奴隶贸易的相关历史,我们真的很难断言作者是真的无视了这些他自己画下的凄惨对比,仅仅将之作为一种呈现而毫不同情,还是感情复杂、内心矛盾,只是被一种国家主义和家族感情戴上了偏心的眼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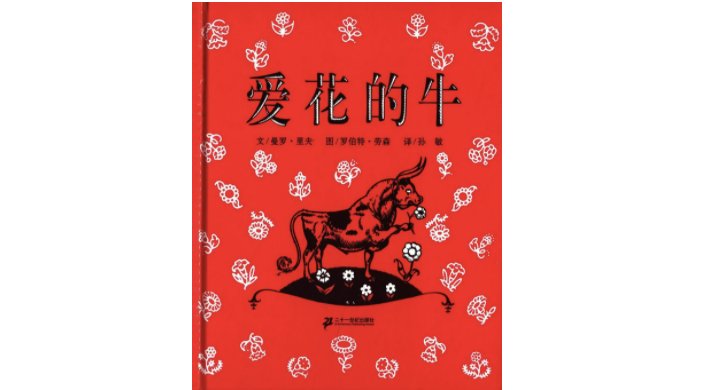
文章插图
《爱花的牛》,[美]曼罗·里夫 著,[美]罗伯特·劳森 绘,蒲蒲兰绘本馆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
尤其是当你知道绘本的创作者罗伯特·劳森正是著名反战绘本《爱花的牛》的插画作者时,会奇怪于当他看到父亲因为战争失去的健全双腿时为什么没有多去追问一句“这场为亲人带来巨大痛苦的战争究竟是为什么?北方军为什么会胜利?”亦如有读者对印第安人取食一节所质疑的:作者“坚强而善良”的祖先们为什么从来没有提问或解释过“嗯,我们繁荣文雅,而同一空间的其他人却在挨饿。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 陈珊|完美伴侣:没有家庭,事业成功的意义又在哪里?
- 宝石|入手翡翠的时候,要反复确认的事情有5件,你可都做到了?
- 墨香铜臭$墨香太爱主角不愿他们跌落道德制高点?笔下人物没有完美只有生动
- 设计师|载入史册的中国大桥,整座桥没有一个桥墩
- 宝玉@红楼梦里,为何晴雯死了,林黛玉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满面含笑
- |工作满5年以上,工资少不敢辞职,说的就是这4类人,当中有没有你
- 求职|30岁小伙失业找不到工作、还没有存款怎么办?可以先看看这三点
- 生存法则#《天道》:丁元英揭秘了2条生存法则,能做到其中一点将来就穷不了
- 周作人!与鲁迅通信250封,在周家住到30岁,她为何没有成为鲁迅的恋人?
- 钻石!人造钻石和天然钻石几乎没差别,可以量产,为何钻石价格没有降!
